6月15日,由东方出版中心发起的东方读书会第16期活动——“见字如面:书信里的灵魂相遇与精神家园”图书分享会,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薛舒,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书评人马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项静,围绕三本书信类图书——《亲爱的奥利弗》《何处为家》和《查令十字街84号》——展开讨论。其中《亲爱的奥利弗》和《何处为家》是东方出版中心新成立的图书子品牌“耕泽文化”出品的两本引进版新书。以下为本次活动嘉宾发言内容整理摘要,均已经本人确认。

活动现场
项静:分享会的题目是“见字如面”,因为这三本书都是书信集。现场很多读者应该都是经历过书信年代的,更年轻一点的朋友没有经历过,但肯定在影视剧或者文学作品中看到过这样的交流方式。 今天我们更多使用即时性社交媒体的交流方式,这三本书让我们回到一个以书信作为主要交流方式的时空中,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写信可以把它置换成书写或者自我表达,是一种很沉静的表达,它跟我们发微信、传达一种信息和指令的迅速抵达,有很大差异。我在阅读这三本书的过程中,重新回温了很多以前写信和收信的感受,并且能够在别人书信交流里面唤起自己和过去时代的一些记忆和情感。这是一种特别的阅读之旅。首先请两位嘉宾谈谈阅读感受。
薛舒:我第一本看的是《亲爱的奥利弗》,腰封上写的是“与《查令十字街84号》一脉相承”——其实《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我很早以前就看过了,而且是先看的电影。既然说是一脉相承,我就想先要温习一下《查令十字街84号》,便把这本书找来,然后再把电影找出来。 我温习了一遍,发现在《查令十字街84号》电影和书之间,书就像一个剧本,戏中的男女主角分开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在纽约,一个在伦敦,两个人通过信的阅读,相互之间倾诉。这种看书跟看电影的感受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感觉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先不要看电影,先看书,因为书会给你更多的想象空间。海莲给弗兰克写信的时候,她是带着某种情绪的,你从她的语言当中就可以看出来。那么你在读的时候就会想象海莲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情,她会有撒娇的感觉吗?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你会想象海莲长什么样,弗兰克又长什么样?如果你先去看了电影,那么,你对他们的形象就已经固定化了。所以,我觉得先看书比较合适,留给你更大的想象空间。

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剧照
那么读到《亲爱的奥利弗》的时候,非常对我的胃口,为什么?因为我先生是复旦生命科学的科研工作者,在我们家充满着科研的气氛,我的儿子、我的先生都是理科生,所以平时跟他们探讨的时候,我一定要加入很多科学思维,不然的话他们会嘲笑我,说我是个感性的人,是个不讲逻辑的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很多疑问都会去问我先生。这本书是关于神经学、关于立体视觉的。我们其实有很多疾病,它可能不影响我们的整个生活。比如说色盲,可能影响一些人的职业选择,考大学的时候,若是色盲,有些专业是不能考的;还有一种,我是个路盲,就是说头脑里面不能把走过的路进行地图式的反应。还有书里面写的“立体盲”,比如几何你学得好不好,你如果说小时候几何学得很好,我相信你肯定不是立体盲,如果几何对你来讲是一个最难的学科,也许你要给自己测试一下,你是不是立体视觉这一方面有所缺失。 有些小孩出生之后眼睛的发育不够全面,会出现对眼、斜视,因为两只眼睛的聚焦点不能同时聚焦在一个点上,看物体的时候,它无法反映出一个三维的空间感。这样子的话,他看一切就都是平面的,比如说我跟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我们中间是有一个距离的,但是没有立体视觉的人看起来就是个平面,大家都挤在一个平面里面,感觉很拥挤。
《亲爱的奥利弗》中,苏珊就一直是这样一个立体视觉缺失的人,从小到大她学习的时候很困难,学开车也很困难。但是到48岁的时候,她因为连续的治疗,有一天有了立体视觉,她欣喜若狂。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仿佛就觉得我跟她有同样的体验。就是说,也许我不是缺乏立体视觉,我缺的是另一种东西,但是我们在获得某一种感知世界的能力的时候,突然我感觉到了,我发现我感觉到了这种新型体验,我觉得苏珊表达得特别好,她在给奥利弗写信的过程当中不断强调和不断倾诉,我感觉到了这个世界的与众不同,其实不是与众不同,而是与她过去的感受不同,而这种不同可能是跟我们每一位拥有立体视觉的人的感受不同,她就觉得很兴奋。她的那种感受力也表达得很好,我觉得她很会写,她在信中讲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伴随着奥利弗。奥利弗年纪比她大几十岁,跟她通信时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检查出得了癌症,身体越来越差,他的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他在向苏珊描述他所看到的世界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对自己的一种精神上的治愈。他们相互抱团取暖,然后相互感受。苏珊是个神经学家,奥利弗是一个医学桂冠诗人,他们的感受力、他们共同能理解的是属于科学的。
另一个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是视觉和身体的隐秘缺陷,他们相互都能够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彼此理解的相互通信,而且持续那么长的时间。特别可贵或者说我特别喜欢的苏珊身上的一点是,她在给奥利弗写信的时候不断在寻求让奥利弗快乐,因为他年纪大了,他生病了,他在走向失去一切的过程中。她的那种想让奥利弗也同样感受到快乐、欣喜,甚至是忘记病痛,不要让他沉浸在病痛中的善意,挺让我佩服的。并且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人,特别有感受力的人,也能够共情到别人并且去体验别人的情感的人。150封信,写了十年时间,我觉得信能写到这个份上,可能我们很难有人能做到。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当我们在写信的时候,我们写下的是真实的自己的生活,还是写下的是打开心灵之后挖掘到生活背后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善于去挖掘生活背后的东西。有时候这本书就会给我这种刺激,我们在写信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感觉到词穷,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是什么都可以写的。所以《亲爱的奥利弗》是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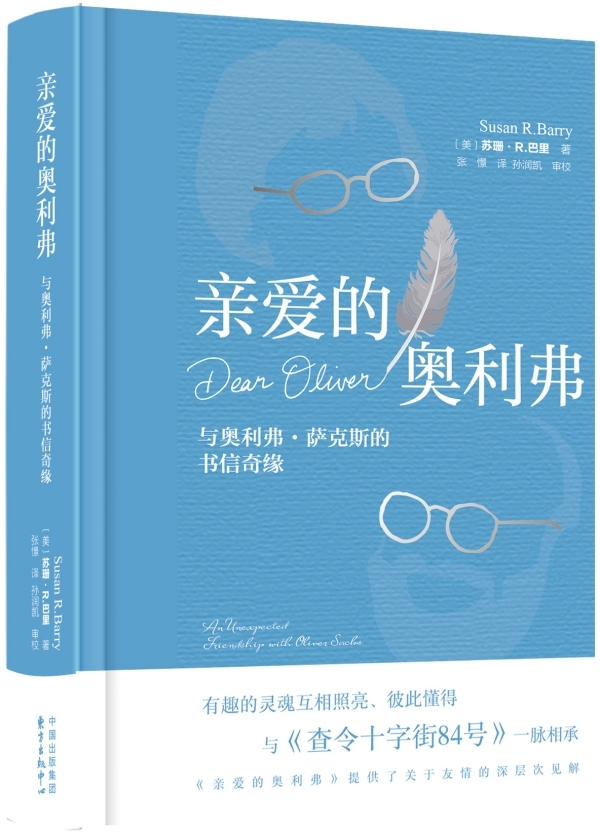
《亲爱的奥利弗:与奥利弗·萨克斯的书信奇缘》,【美】苏珊·R.巴里/著 张憬/译,东方出版中心·耕泽文化,2025年4月版
然后再看《何处为家》,是两个文学家相互之间的沟通,这可能跟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加接近,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在这两本书中,我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的性格,他们毫不掩饰地在相互来信中吐槽也好,批评也好,赞美也好,我的脑子里面就会描摹出一个男主角叫唐纳德的样子,还有女主角叫雪莉的样子,就像看《查令十字街84号》那样。所以说,“见字如面”,虽然说我们不是跟他写信,但是我们看他的信就能看到他的脸,这是我自己脑中的想象。
马凌:特别佩服薛老师的口才,表达得非常好,我也谈谈我对三本书的感受。《查令十字街84号》,大家知道是世界级的名著,光在国内就出了好几个版本,我问了问我周边的人,大部分人都看过那本书。我昨天晚上为今天的分享会重温了一下这本书,确实写得非常好,信都很简短,大家会发现海莲就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白羊座女性——充分地表达自己。弗兰克跟她的性格正好相反,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但是我们说性格是有互补性的,可能就被海莲给感染到了,然后他也变得比较开放一点。然后两个人这种对于文学的热爱,对于版本的热爱,以及生活上的互相帮助,特别是海莲对于弗兰克的帮助就看得清清楚楚,如薛老师所说的也非常富有戏剧性,是特别温馨的一部小书。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爱书的人都会喜欢这本小书。
因为我对数字比较敏感,我还特意看了看海莲当时买书的钱,那多半是一块多不到两块,零零碎碎的,最大的一笔只有18美元75美分。其实算下来她一个月可能会挣200美元,这钱也不算是大钱,比较贫困,她一直没有凑够路费去伦敦看一下弗兰克,这也是让人蛮伤感的一件事情。换过来想,我有这样的感觉,两个人不见面其实也挺好的,因为他们互相成就,且两个人中间横隔了大西洋,每封书信都要耗一定的时间,永远不见面,其实也挺好,就是在心目中永远是想象中的对方最好的样子,可能挺符合我们所说的“笔友”。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过笔友?我还不止一个笔友。我觉得笔友往往“见光死”,因为书信当中表达的都是最美好的方面。综合起来,(《查令十字街84号》)很符合我对笔友的想象,是挺感人的一本书。
至于《亲爱的奥利弗》和《何处为家》,我觉得“耕泽文化”在新成立伊始就能连续出版这两本书信集,装帧精美,非常雅致,编辑非常用心,我很感动。特别在《亲爱的奥利弗》这本书当中,我最喜欢看的是他们的手迹,书信原始的样子,真的是有“见字如面”的那种感觉。
我们看到(《亲爱的奥利弗》和《何处为家》)一本蓝色一本红色,蓝色的是科学家的对话,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科学家;红色这本是两个文学家的对话,一个是小说家,一个是研究型学者,正好形成对照。令我意外的是,我发现科学家们写信的文学水平超过了我的想象,特别是苏珊的信绝对是有文采的,写得又真挚又自然,真的是写到了内心深处,把生活的情绪也挖掘得特别透彻。再来看这本书后面的四张照片,你都很难想象是没有任何修饰地、没有任何美化地,直接就把生活当中的场景非常随意地放上来。换句话说,书信交往已经渗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是非常自然的,不需要装腔作势。
而且他们长期的书信往来,不仅是通信关系,两家人、我们说的朋友圈都融合到了一起,把更多的朋友带进他们的交往当中,一起吃饭、旅游。比如说苏珊,她有一顶非常有趣的帽子,可以导航,她就把这顶帽子介绍给奥利弗。这些全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夹杂着对于科学真理的探寻。这种轻松的奇妙的融合,真的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家生活的世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科学家,我是从小生长在哈工大的家属区的,我赫然发现那些叔叔阿姨现在都是什么院士、科学家了,换句话说,科学家也是常人,我们就是应该看到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面,他们怎么成为科学家的,怎么通过一点点的努力达到后来的成就的,大家看《亲爱的奥利弗》这本书就可能会有所体会。
通过他们俩的书信(我们知道),在两个人通信的过程当中,双方都有极多的著述。我觉得这是双方彼此促进的。苏珊写了好几本书,奥利弗写得更多,真的是良朋益友的关系,互相支持的关系。所以两个人的生命当中如果缺了彼此,对对方可能都是一个损失。更感人的是,他们真的就是纯纯的那种友情,我觉得没有任何暧昧的成分,今日看来就更加难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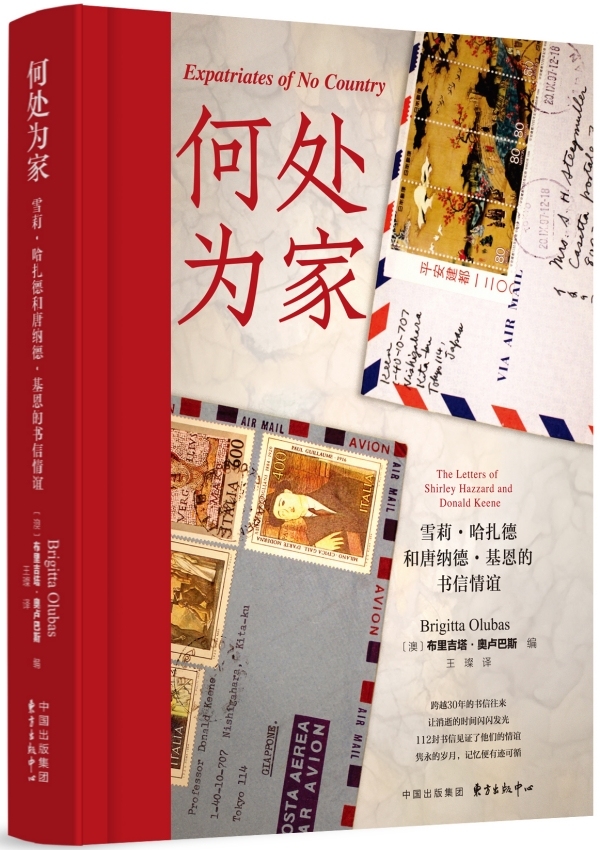
《何处为家:雪莉·哈扎德和唐纳德·基恩的书信情谊》,【澳】布里吉塔·奥卢巴斯/编 王璨/译,东方出版中心·耕泽文化,2025年5月版
另外这本《何处为家》,确实能看出性格来。小说家雪莉的文笔更胜一筹,而且她写的信往往都要更长一点!她提到对于小说、对于戏剧、对于景观建筑等的感受,也都非常细腻。基恩是男性,他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也是一个专门研究日本文化的专家,但他身上可能更多体现的是大学教授的那种我们说比较清冷的气质。这两人气质并不完全一样,看这本书我特别觉得有趣的是,基恩默默被雪莉影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个研究日本文学的专家不一定对19世纪的英国文学感兴趣,但我觉得基恩被雪莉影响到了,他一本本地在看19世纪的英国小说,然后一本本向雪莉汇报:我看了哪一本,我目前在看哪一本。恰好那些书,我看起来都非常眼熟,就是目前大家很少看的、但在我心目当中很重要的作品。如果不是为了和小说家雪莉同频,我觉得基恩未必会看。
还有,看这本书一定要看到字里行间。他们通信当中有时候是有中断的,有的中断有可能是两人见面了,有可能在某个地方相遇一起去旅游了。你可能会进一步想,为什么到后来会看到基恩更加努力一点,写的书信更多,而雪莉好像回信更少一点呢?因为她遭受了生活的打击,她的老公去世了,老公跟她是志同道合的,所以可能给她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创伤,她的回应就没有那么多了。无论如何,他们一直写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是很让人感动的一本书。
如果大家喜欢歌剧、喜欢文学、喜欢旅游,可以认真看一下这两个“世界主义者”、走遍世界各地、不在自己母国居住的两个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举个例子,雪莉吐槽过特朗普大厦,大厦在1983年落成的时候就非常的土豪,她直言不讳地认为特朗普大厦太丑了。他们会把对周围很多事情的观感、各种感受都写到书信当中。
这三本书信集看下来是别有况味的感觉,让我们回到了见字如面、用纸笔写信的那个时代。
项静:我也讲一下自己对这三本书具体的阅读感受。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中是把书信看得特别浪漫的,因为书信就是远方的消息,古代人或者是在通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都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很少有机会去远游,到宋朝的时候才有大量的官员开始游山玩水,但是他们即便是在做官的路上、在旅行的路上,也特别喜欢把自己见到的东西写给自己的朋友、写给自己的家人,所以书信带有一种浪漫气息,包括我们把信件称为“尺素”“锦书”,优美的称呼中带有超越我们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气息。这三本书虽然都是外国的书信,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有那种浪漫传奇的色彩在里面,因为书中的两人之前应该都是不认识的,是不相识的人在某一个偶然的机遇下相识,比如说《何处为家》中的两个通信者雪莉和基恩,他们的相识是在共同的一个朋友的葬礼上,这具有偶然性,等于是一见如故。之后他们就长达30年,持续不断地通信。这绝对是一个传奇,普通人都很难拥有这种奇遇和经历。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是一种非常传奇的生活方式,而且带有浪漫的色彩,所谓的浪漫就是我们很难再获得、很难再拥有这样一种交流的方式。
《亲爱的奥利弗》这一本我觉得也是非常传奇。刚才薛老师在介绍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两个主人公的故事,小说都不敢创造这种戏剧和张力,一个40多岁的女性生物学家,也是神经学家,突然获得了立体的视觉,并且见到了在学术界非常有名的奥利弗,把自己的症状向他做了大量的描述。比较特殊的是,这三本书中的书信写作者,都有写作的习惯。苏珊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她能够把自己的症状描述得特别清楚,把以前患病的过程非常详细地提供给另外一个研究者,所以他们能够变成病患和研究者的关系,同时也变成像马老师刚才所讲的互相促进的关系。在这种互相交流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变成一个书写者,变成一个很好地给世界提供帮助的人。这是本书在两人交往交流、互相疗愈之外,对社会提供的一种善意,也是他们两个人交流的基础,她希望把自己的症状、疗愈自我的过程,传递给更多的人。苏珊后面也接到了很多跟她有相同症状的人给她写信,它变成一个自我生长的故事,不仅是两个人的故事,而且变成一个群体、变成很多陌生人之间的协助和支援。
刚才薛老师说到书信背后的东西也是这三本书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它们背后都还是有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东西。像《何处为家》中对世界主义的考虑,这两位作者都不是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我们很难在自己的出生之地,从小长到大,从小到老,大家都是四海为家,或者都在世界上不断移动,不断变换自己的位置,包括身份的变化、年龄的变化、居住地的一化,我们怎么样去建造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是《何处为家》这本书讨论的主题。我们在世界上要能够抵抗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要超越自己的现实,或者是像《亲爱的奥利弗》中所释放的善意,愿意帮助别人。当然我觉得像《查令十字街84号》更为明显,他们到最后也变成一些群体之间的交流,在战后物资比较缺乏的时候他们互相帮助,海莲会寄很多东西给在英国生活有一点困难的那些书店职员,包括他们的家人,甚至他们店里边的工作伙伴都变成写信人。所以我觉得,书信的本质其实就是自我表达,并建立一种深厚的关系,因为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今天的人是有一点孤独感的,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看起来是越来越方便了,点一个外卖,外卖员就可以迅速送到家门口,发一个微信,马上就能够获得一个指令,但实际上中间省略掉太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边,是有价值和意义留存的,就像他们经过那么漫长的物理距离,才能够得到一个好友的关心,才能够看到好友的身体状况,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多么琐碎,多么没有实质感,但是这些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可能特别需要的东西。
我看着这三本书信集,经常会想到这样一些话题上来,我就觉得人到底是什么?人是需要一些复杂性,而不是特别简单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今天还愿意进行自我表达的重要内容。虽然说我们不再写信了,但是我们在写微博,我们在发朋友圈,甚至我们在以化名的方式交流,像笔友,当然我们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可能也会认识到或偶遇到一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我觉得自我表达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书信类图书的出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给我们提供一种思路(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建造自己扎实的生活。我特别喜欢《何处为家》这本书,因为写信者的交流其实是一种闲谈闲聊,闲谈闲聊也是很重要的,它会中和功利主义带来的焦虑。这本书有一句话,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工作和爱,爱是很广义的范畴,对朋友的爱、对家人的爱,有各种各样的爱,都能够建造生活的有机感,我们才不会被某一种情绪给框住或是僵化。《何处为家》里面这两个人的生活让我忍不住自问,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简单?他们有这么多的倾诉和交流的欲望,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可以告诉别人,这也是一种打开自我的方式。只有打开了自我之后你才有新鲜的世界,才可以告诉某一个你的“收信人”。
薛舒:我在看这三本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体会,这三本书都是一男一女在通信。我在看《查令十字街84号》电影的时候,片尾写的是爱情片,当时我就质疑了,我心里在想他们是爱情吗?有没有太浮夸了?可能电影想要吸人眼球,如果没有爱情的话,这两个人在干什么,有什么好聊的呢?所以说它用了“爱情”两个字来吸引观众。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想,他们在被相互温暖、相互理解的时候,会不会产生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情感上的依恋,这种情感上的依恋究竟是什么? 比如说在《亲爱的奥利弗》这本书里面,苏珊的先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并且经常给她一些建议,包括她的导航帽子都是苏珊的先生给她做的。那么她在描述这些自己获得了立体视觉之后的心情以及特别有意思的表达的时候,就是苏珊本人特别有灵气的一种写作能力,包括发现世界的视角,她这种灵动的东西是要被人欣赏到的,才有表达的欲望。就好像我去跟谁描述一个故事,他要是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不理解我想说的是啥,我以后就不想跟他讲了。那么我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苏珊会在情感上对奥利弗有点依恋,而这种依恋我们不能粗暴地把它定性为“爱情”,这是不对的,是粗暴的,或者说是狭隘的。我在看男性和女性之间通信的时候,尤其令我感觉到珍贵的,是他们的克制,《查令十字街84号》中的弗兰克是克制的,白羊座女生海莲也是有所克制的。海莲在给弗兰克写信的时候很彰显她的性格,但是她彰显性格的时候,我觉得她依然是有所克制的。这种克制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同时也是一种自尊。“我是有自尊的,我对情感的理解是有我自己的理念的。”所以这几本书中的男女给我的感觉,男人都很绅士,女人都很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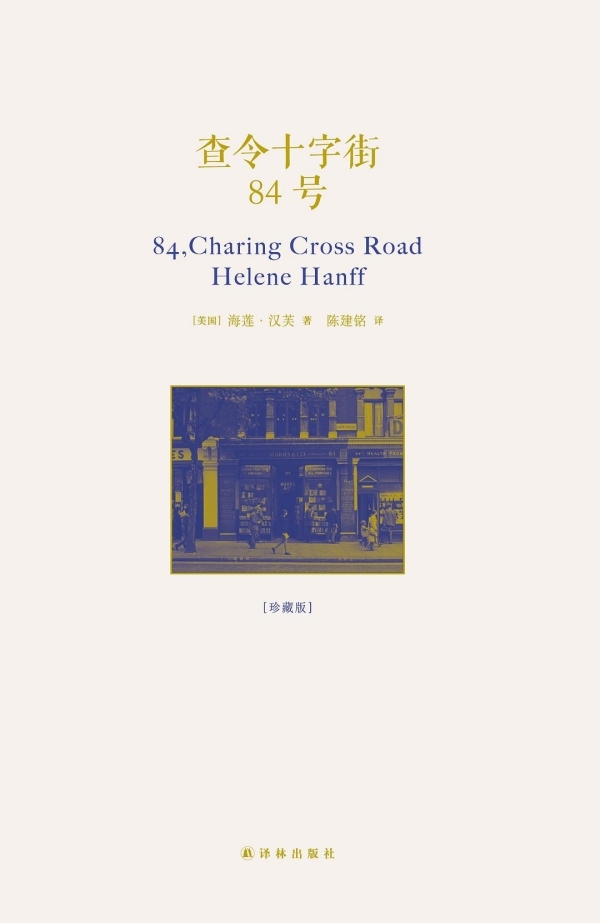
《查令十字街84号》,【美】海莲·汉芙/著 陈建铭/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5月版
马凌:我一直说灵魂伴侣跟生活伴侣未必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将是人生中最幸运的事情。可能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幸运,我们跟生活伴侣能够白头偕老,灵魂伴侣则未必能有,或者说有也未必能长久。但对于灵魂伴侣,你不要把关系搞得复杂,这可能也是人生当中的一桩幸事。我觉得像弗兰克的夫人能够允许他的先生有这样一个灵魂伴侣,并且不公开表达她的嫉妒,是有一个宽广的胸襟的。
项静:其实这三本书可能都会有想象的空间。我们的世界十分宽广,同时也非常复杂,爱情相对于这个丰饶的世界来说,我觉得是微不足道的。回到《何处为家》这本书,我特别喜欢书里的那句话:爱和工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基恩和雪莉两个人交流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讨论自己的工作,扩展自己生活方式的各种各样的纬度,他们去逛画展,去博物馆,去看各种演出,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刚才马凌老师说到灵魂伴侣,我觉得这是一个称呼,是一个说法,我们的灵魂是有很多方向的,需要非常多和你契合的人,有的人可能在读书上和你契合,有的人在写作上和你契合,有的人可能在生活方式上和你非常契合。这些书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释放自我开掘自己,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很丰富的人,如果我们不去观察自己,不去表达自己的话,你就是一个普通和重复的人。这三本书里的人在写信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反复看自己的生活,反复观看自我,在看的过程中,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投入思想碰撞的过程。在这三本书信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成长,每个人都不再是最初开始写信的自我,变成一个更会表达的自我。理解和爱是一种多维度的情感,它介于友情、爱情、欣赏、仰慕、崇拜等等之间,当然他们都非常坦诚。
另外一点,为什么他们能够持续这么长的书信往来,一定是跟他们的兴趣有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吧。我们为什么有很多友情都是渐行渐远或者是迅速中断的,可能是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维系它。任何有质感的关系都需要有一种共同之物、一个研究对象,比如说文学,比如说写作,比如说医疗。
薛舒:我当时看《亲爱的奥利弗》的时候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他们的很多想法落在纸面上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是最诚实的。一开始的时候苏珊说自己是48岁获得了立体视觉,但是从医学角度研究的话,如果小时候没有纠正,长大了是无法恢复的。奥利弗也是持这种观点的,所以他要来亲自见她,然后来测试她是不是真的获得了立体视觉。他要看她的医疗方式到底是什么,让她居然能够人到中年以后才获得立体视觉。他其实是不相信。他来给她做过一次测试之后,依然没有得到完整的或者说是完全可信的答案。好,那么接下来苏珊给奥利弗写信,奥利弗回信,我感觉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直截了当,他是有所保留或者说避而少谈。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写信能持续这么久时间,他写来写去不可能样样迎合,虽然说是志同道合,但是不可能每一样都认同,也不可能每件事两个人都是同样的观点,一定会有冲突的,或者说会有分歧的。 那么我们写信,也是像在维持一个家庭一样,是一种相处。人和人的面对面交流、家庭生活,有的时候必定有一个人在退让,有一个人在试图去更理解,对方想想他也是有道理的,有一个人就慢慢改变了。这是一种维系,也是一种相处。写信其实也是要有这样的相处的。
马凌: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第一珍贵的一手资料是日记,因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的,当然这是最有质量的。但后来发现也有问题,就是那些认为自己将来会成名的人,他会有意的写那种不是真情实感的日记,只写那种给后人看的日记。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总之,日记的重要程度大于书信,书信是第二位的,往下才是传记,再往下是别人的研究等其他类别的东西。书信的诚实度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不是百分百的诚实度。有时候我们可以把书信人格叫做“第二人格”,跟你日常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肯定有大量自我美化的成分,当然也有自我吐露的需要,是一种综合体。为什么好多笔友会“见光死”,是因为会发现他生活当中的人格跟他在书信当中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就说明这位笔友是有写作的天分的(笑)。所以,书信是很有趣的一个研究领域。
最后,我有一个感慨,今天是父亲节,我也想倡议一下,能够提笔写信的朋友可以给自己的父亲写一封笔墨书信,这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
吉祥起名网 吉祥起名网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