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互联网上姜文“神”的形象在极速跌落,是一场“作者之死”的现实操演。《让子弹飞》的“教科书化”一度令姜文登上神坛,但内因上2018年《邪不压正》反响平平加上七年未有新作,外因上随着国内文艺界性别意识的觉醒与观念主潮的转变,《你行!你上!》上映前后的姜文和其电影,基本已被祛魅。尽管依然有人一如既往地“故作高深”地解读《你行!你上!》,但平庸的票房与惨淡的关注度似乎正说明“姜文”这个“本体”已经过时了,《让子弹飞》是历经时间考验、永垂不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姜文不是。
但其实,《你行!你上!》是值得一看的:至少在现在这个纯粹被算法控制的商业电影市场,《你行!你上!》难得是独创性的(original)的,它依旧还是姜文的作者电影。它癫得可以,尽皆过火,尽皆癫狂,充满着不顾一切只管向前、摧枯拉朽改造世界的远视主义精神,近乎成为一种贴近成功学的反动影像,将姜文的美学和行为艺术内核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音乐家传记电影,它几乎又反音乐又反人性,音乐和人性,都只是艺术家表达“向前”的可以被随意牺牲的工具,郎朗本人,也只是饺子皮罢了。
然而批判这些的同时,你又很难忽略当电影一本正经的“向前”,亢奋到一种极致的荒谬的时候,那道难以抹去的无助与悲凉,那是艺术家无法摆脱的某种属于人性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我看到了姜文一直在坚持的被称作“爹味”或者说“老登”气质的必然沉沦与这种气质内在核心的荒诞。于是,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反思,但更像灭亡前的绝望与疯狂。
那也许,现在也是回头梳理姜文电影美学的时候了。
与“赢学”“速胜论”一体两面的“不知所措”
也许,姜文本人会觉得《你行!你上!》不被主流年轻人青睐是很奇怪的:这明明是一部很贴合时代精神的“赢学”电影啊。主角郎朗17岁前的经历恰好是“速胜论”的赢学范本,他天才出身加勤奋至极,迅速确立了人生目标,排除一切干扰,父母牺牲自己的人生为其铺路,于是,对郎朗所有的考验都以郎朗无可置疑的胜利告终,几乎没有什么真正可以打倒他的困难,再大的挫折也只需要深吸一口气,再向前顶一下就行了,赢,赢,永远都是赢——这样的电影不是很应该受到当代互联网的喜爱吗?
所以,矛盾正在这里:姜文也许是太了解年轻人了,于是也就等于太不了解年轻人了。年轻人是要“赢”,要“一直赢”,但人与人交往时,其实并不接受凭空的灌输与“不劳而获”——获取的过分随意将颠覆“赢”的含金量,而在姜文电影的观演情境里,这更是成了一种“老登”的施舍。这是不行的,年轻人不受嗟来之食,不是唯心主义、无视现实的傻子,你不能凭空就让他们“赢”,而是要煞有介事、煞费苦心地创造一个“合理”的“赢学”情境才可以,而且这种“合理”,不一定是现实的合理,而是符合年轻人笃信的电子游戏化现实的合理才行。
在这个情境里,主人公确实也一直在“赢”,但主人公必须是和大家一样的普通人,怎么能是亿分之一的郎朗这样的天才呢?谁能代入这样的天才呢?其次,主人公确实要战胜所有的困难达到“赢”,但这种“赢”的标准必须是明确的,看得见摸得着也符合常理的,这样才方便主人公“打怪升级”,一步步稳扎稳打按部就班地“赢”,而《你行!你上!》中郎朗遭遇的考验与困难,却几乎都是玄妙无形的:我们无法分辨乐曲演奏细微上的好坏,哪怕和我们说清楚“不能弹错一个音”,刻画顶级指挥家的怪癖和变态,我们也觉得这是过度严苛不合理的升级条件,必须“炎上”开发商,改为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标准——可这是艺术啊,哪里有像电子游戏那样公开明确的标准呢?
说到底,“赢学”和“速胜”,是在宣扬最广大的普通人能“赢”的方式,而《你行!你上!》本质上是一个“天才”在赢,他为什么赢,因为他本来就是天才,而我们谁也不是这样的天才。甚至于,这种“天才赢学”比权力与财富造成的特权更令人破防,至少面对权力与财富,我们还有一整套左翼价值观作为武器,还能依靠朴素的正义感制造人多势众,哪怕其实解决不了但至少有一个能够改变的幻觉假象,你面对“天才”能说什么?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是他对,一切的义正词严都没有了,只能乖乖闭嘴回哥布林巢穴——此时,怎么可能还能指望观众们去带入呢?
其实可能,电影的宣发营销和一些姜文的粉丝也都意识到了,于是他们敏锐地将“天才郎朗”这一主角,通过经典的姜文“隐喻电影”运作,再次将姜文的表达拉回了中国近代史。隐喻一套一套也不能算是毫无道理,不少解读绝对也贴中了创作者的潜意识表达,似乎这样就能让观众们代入了……
可是,这样的解读却又太“白”了,成了“故作高深”,更是在2025年这个因为《红楼梦》癸酉本塌房的“索隐派倒台”元年,沦为自娱自乐的笑话。又是近代史,姜文老师不谈近代史不会说话了吗?曾经被大家奉为“教科书里没有”的隐晦表述,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成为“显学”。很多人不愿意再相信《你行!你上!》是隐喻了,一方面是实在是厌倦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如果继续按这个隐喻思路读解下去,《你行!你上!》不仅过于直白,其表达深度都会触及难以为继的枯竭境地,很难想象姜文还要怎么再把“故事”说下去。如果他已经是总设计师了,已经是“儿子不感谢他”的终极悲凉了,已经从描述“爹”到亲自扮演“爹”了,曾经切实可触的理想主义已经转变为玄之又玄的艺术崇高境界了,这个故事还要怎么再讲下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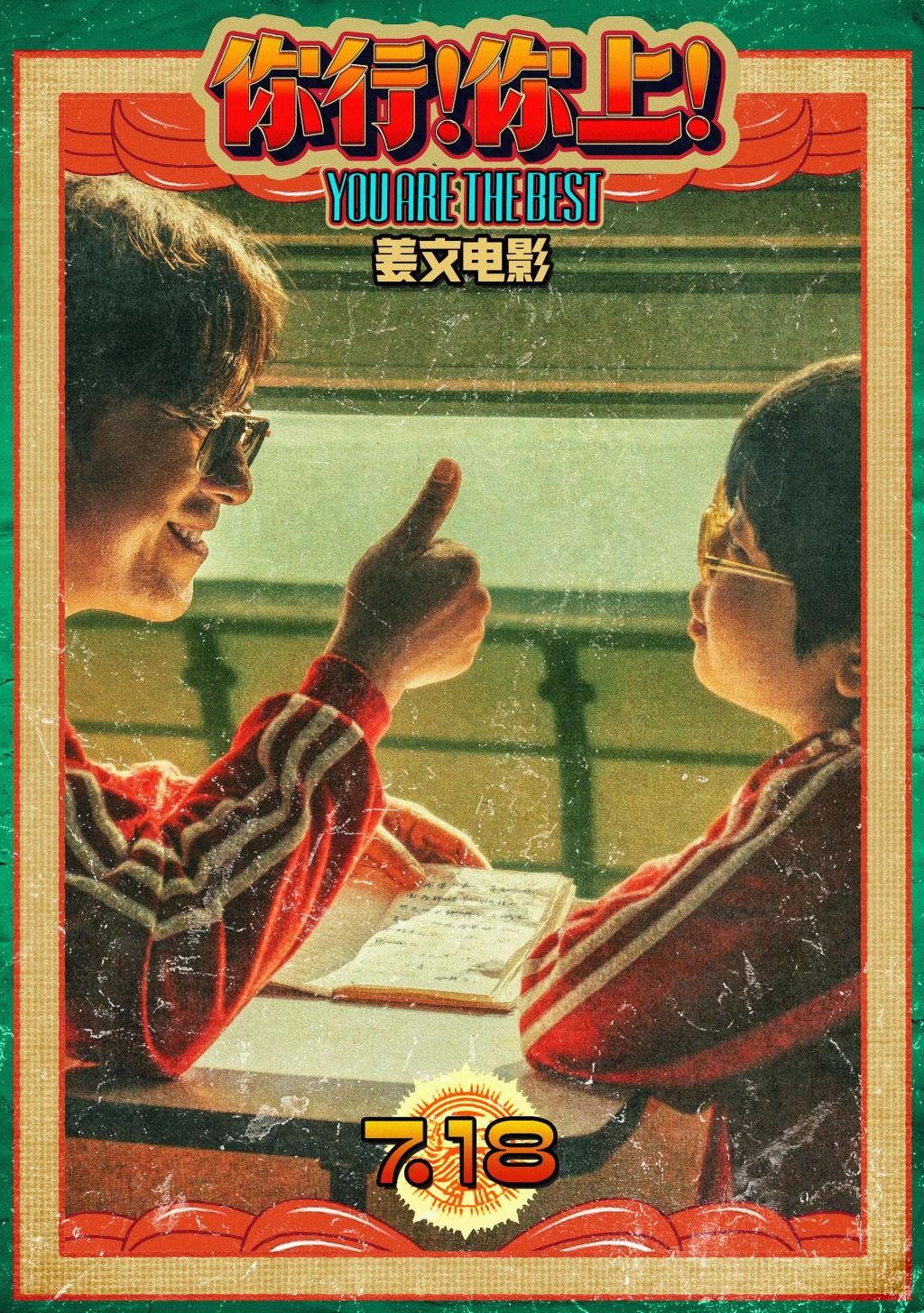
电影《你行!你上!》海报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被隐喻的对象现在正处于一个“不知所措”的境地,才让姜文的故事无法继续说下去了。如果17岁就已经触摸到了世界之巅,一如现在的我们已经走到了最前沿,那我们该怎么继续前进呢,从哪儿前进呢?无论是谈论“天才故事”还是讨论所谓的隐喻,《你行!你上!》的故事都讲到了终点:赢学一体两面的背后,正是“赢了”之后的不知所措——而我想,大多数观众并没有觉得自己身处这个“后赢学”的境地中,也何谈共情;哪怕,他们相信我们的国家已经来到这个境界了,但他们自己没有。
即是天才的,也是即将衰落的
但姜文是可以共情的。甚至不是共情,而是他自认就是天才,这些天才的故事就是他自己的故事。在他的世界里,“战胜自己”“与自己搏斗”不是某种增强自信的心灵鸡汤,不是知道自己不行但要提升自己的自我鼓励,而正是作为天才所能做的最宏大、最深沉、最艰难的斗争,是尼采所谓的“超人”如何引领世界并实现自我超越。那些质疑的“声音”都太俗了,他们怎么能够理解天才的痛苦呢,怎么能看出郎朗看似毫不费力但却竭尽全力呢?
经常有人询问姜文电影中某些具体的隐喻,似乎想通过他的回答来解释他的创作,但至少我看到,他的回答往往是模糊的。有人说这是他在故意掩盖,但也许是创作者的某种共同的敏感,我始终觉得他是真诚的,我偏向他其实对很多问题并没有准确的答案,很多创作的来源必然只是“直觉”的。20世纪上半叶,认为直觉是天才创作的唯一方法的美学思路最终导向了精英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个因为历史造成的悲剧,也形成了人们对天才和艺术无意识的压迫和姜文的“委屈”。
我相信,正是这种天才的自我认知和这种认知与平庸的外部世界无限对撞的痛苦,让姜文从2007年《太阳照常升起》开始的近二十年,一直在拍同一部电影。他甚至是故意的,可能在他看来,只要《太阳照常升起》还没有被彻底理解,他就要继续把一部部电影都拍成对《太阳照常升起》的注解,直到所有人都理解《太阳照常升起》为止——可与这种天才的疯狂同步的,又是他的绝顶聪明,他深深明白《太阳照常升起》和作为天才的自己永远是不会被所有人理解的,于是,在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存在主义境地里,他拍了《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你行!你上!》,始终在说服自己我还有话说,直到他的人性一面将他的绝望、无助、虚无与存在的荒诞和盘托出。
《太阳照常升起》是姜文电影的“原典”,在这之前是对它的准备,在这之后都是对它的注解。因此,将《太阳照常升起》解读为政治电影是片面的,它不是浅显的点对点的近代史记录,而是一场场梦境和一个个寓言。视觉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建国初期革命题材油画风格的独特色彩:它既是纪实的,却又是被一层理想的滤镜所美化的,既清晰原始,素朴不加修饰,却又过分干净,充满晕点和梦幻。伴随这种视觉特征,姜文的镜头始终是“运动”着的,是有一个明确的视觉起点的,无论是长镜头还是在《你行!你上!》中呈现的超级跳切,它都是一个“天才”主观的视角,于是他一切的影像,都有感官能够体验到的时间长度和重量,而绝非抹去感官中介的纯粹视觉。还有音乐,久石让的配乐被他一直使用,那莫扎特影响的《太阳照常升起》的配乐,是在优雅的交响配器基础上的“狂放”,是在浓烈的抒情基础之上的张扬,这是“神”的狂欢,是“神”的悲伤与快乐,而不是人的——
最终,在姜文个人特质明确的视觉色彩、镜头运动与配乐烘托下,是他喷薄而出、不加修饰、尖锐直指人心却又包含着无限情感浓度的文本表达,从文字出发,从躁狂的情绪出发,从北京方言的内生节奏出发,最后走向对现实意境的看似荒诞的彻底超越。很多人提及姜文的艺术风格离不开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但我觉得姜文的荒诞与库斯图里卡还是有些区别,姜文努力描绘的荒诞世界往往不是可以被惊醒的梦境,而恰恰就是他所梦寐以求的终点。也就是说,他的荒诞不是反讽,而是正向的,影像的最后目标不是反思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天才的世界固然可怕,而姜文的可怕更甚:他要把现实,也变成他的世界。
因此,姜文的影像总是有种不可质疑性,存在一个他自我投射的卡里斯马在控制一切,在推动影像走向极致的崇高,这种崇高是不担忧把一切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作为代价的,走向美的极致可以是纯粹的光明,也可以是无限的黑暗,对美的极度痴迷必然是不容置疑的,一种天才惯用的,最伟大的艺术只能源自“直觉”的“超人”思维的运作——至少他会认为,他的所有影像,都是崇高的,或者是为崇高服务的;艺术就该这样,这本来就是对的,然而20世纪的历史进程让这种美学思路在现实历史中死亡了,那些与艺术无关的东西,最终借助社会规训破坏了艺术,也屈害了每一个追求纯粹的天才。
也因此,我在《你行!你上!》中看到了一些明确的失控:伴随着郎国任对郎朗的失控,姜文也对自己的影像和节奏开始失控,并在郎朗最终的胜利面前失语。面对无奈的现实,面对他的艺术表达必然将被现实所戕害的结局,他选择了最后做一次任性的绽放:
他不顾如今文艺评论界对“爹味”“登味”的避之不及,不管不顾如今蓬勃崛起的女性意识而去继续将女性当作纯粹而热烈的欲望客体,他抛弃一切正常观众让这部影片彻底成为天才狂躁的自言自语,让音乐与人性都沦为天才攀登向上,化身超人的工具,这种极致,“不装了”和“彻底疯了”,也许都源自明确的危机感——郎朗从此不再需要他的父亲,从此将走上无法被老一代经典所指导的新路,而他本人,也在做面向超越的窄门最后一次竭尽全力的跨越。
他知道他要不灵了,所以他将最后的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正是因为反思不可避免地到来,路径才被一个天才继续张狂而偏执地依赖;他要最后再尝试一次,他要真正实在地做一次爹,这次爹味和登味的爆棚,正是它们衰落的序章。
我是乐观的。我相信姜文如果还会继续创作,下一部一定不再和《太阳照常升起》有关。因为他这样的天才会认识到,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他所想创造的世界已经实现了,天才也该死了。不是他过时了,而正是他对了,他对未来的预言如今已经是过去,如果继续念叨这些寓言,就将堕落为他看轻的那些遗老遗少。“登味”已然随着年轻人的成长夕阳西下,映照着前路茫茫,明日太阳将照常升起;至于他还参不参与,是另一回事了。
【本文系“樱桃园评论”约稿,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经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