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郝珂灵(Karen Hao)是全世界最早报道OpenAI的记者。2019年8月7日,当她抵达OpenAI办公室时,OpenAI还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但处于快速变化中的公司。那时她是MIT Technology Review报道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深记者,具有MIT工科学位和硅谷工程师工作背景。
报道过程经历了一系列波折。通过在OpenAI的公司受限制地蹲点三天,以及对该公司前员工和现员工、合作伙伴、朋友和其他领域专家近三十次采访,她观察到的是OpenAI的野心如何使其偏离了最初的使命。这篇深度报道刊发后,OpenAI显然并不满意,此后三年再也没有接受过她的采访。
今年4月,在这本书面世之前,Sam Altman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声称将会有人出书抹黑他和OpenAI, 并强调那本书的作者并未采访他。郝珂灵回应道:我就是“那个人”,我在写书的过程中一直寻求OpenAI可以出来接受采访,他们说了几个月“快了快了”,但始终没有(接受采访)。
5月,郝珂灵在持续的业内采访基础上出版了新书Empire of AI: Dreams and Nightmares in Sam Altman's OpenAI(《AI帝国:萨姆·奥特曼的OpenAI的梦想与噩梦》),深入探讨了这家引发AI军备竞赛的公司,以及这场竞赛对我们所有人意味着什么。6月24日晚,她在香港的线下文化空间“过滤气泡工作室”做了一场新书分享,主持人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以下是分享会的文字整理,我们将英文表述翻译成了中文,并对口语表达做了适当的编辑。本文经讲者审订。

6月24日,《AI帝国》作者郝珂灵(Karen Hao)在香港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做新书分享。过滤气泡工作室 供图
OpenAI选择“大力出奇迹”的发展路径,为了最快抢占先机
方可成:我想先请Karen来跟我们介绍一下Empire of AI这本书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那就是:你对于OpenAI、对于Sam Altman发展AI产业的路径持非常批判的态度。所以,Sam Altman的策略,他发展AI的方式,问题究竟在哪里?OpenAI这个公司真的很糟糕吗?如何帮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郝珂灵:很多人第一次接触人工智能就是因为ChatGPT,所以很多人以为ChatGPT就是全部的人工智能技术。但其实人工智能是一个总称,涵盖了很多种不同的技术。ChatGPT这种生成式AI技术采用的是大规模AI模型开发的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在训练这种模型的时候,要用很多数据、很多能源、很多资源来开发这种人工智能。
方可成:所以之前大家并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做的?
郝珂灵:以前的AI模型都是用在数据、计算、能源方面都更加高效率的方法。但Sam Altman和其他高管——前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Greg Brockman,还有Elon Musk——刚开始创办OpenAI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这个特定的发展轨道。他们当时认为,最快在AI发展方面达到第一的方法,就是采用规模化的方法,用很大的规模来训练更好的模型。一旦他们选择了这种规模化方法,就必须用很多能源、很多资源来做人工智能。
方可成:所以就是“大力出奇迹”。他们其实也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就是要用更多的数据和能源。
郝珂灵:是的,这是一种非常暴力的方法,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创新性。当时OpenAI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方法其实被很多比较有名的科学家看不起,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真正在探索新的技术来发展人工智能,而是用已有的技术来暴力突破,只是加更多数据、更多资源和能源,把规模扩大。
虽然当时那些科学家看不起这种方法,但后来OpenAI获得了巨大成功,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忘记了以前那种轻视的观点,反而很羡慕OpenAI这种方法。我写这本书,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描述这段历史,因为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以前人工智能领域有非常多样化的观点。但现在,所有的大公司,特别是美国的所有大公司,在发展人工智能时,都在用这种大规模模型开发的方法。
方可成:有人可能听说过一些相关的术语,比如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之类。这些是属于OpenAI的方法还是属于更高效的方法?
郝珂灵:深度学习既包括OpenAI的方法,用很大的数据集,也可以用比较小的数据集,它们都是深度学习。OpenAI当时就是用的这个技术,但他们改变了规模的数量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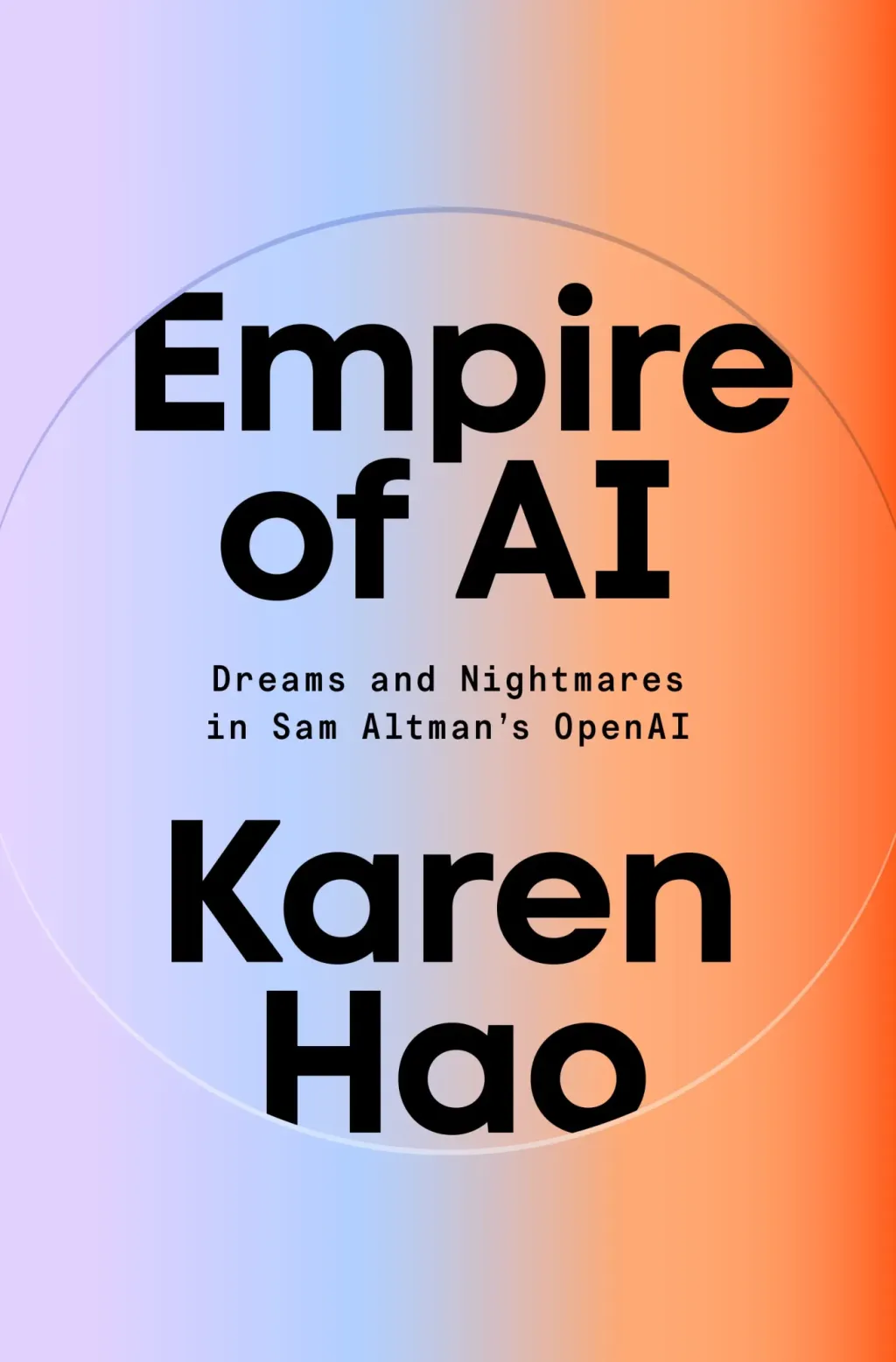
Empire of AI: Dreams and Nightmares in Sam Altman’s OpenAI书封
方可成:你刚才说这是四个人的共同决定。
郝珂灵:也可以说不只是这四个人,但是这四个人每个人对于为什么要用规模化的方法去做,都有不同的观点。对于Ilya Sutskever来说,他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做反主流的事情。当时这种大规模的方法被认为不足以开发AI,但他就想要这么去做。作为四人团队中唯一的科学家,他就自己做决定说,我们要追求这个方法。
至于Sam Altman、Greg Brockman和Elon Musk,他们都是硅谷企业家,喜欢闪电式扩张、创造垄断的公司,所以他们也喜欢这种规模化方法。虽然他们没有科学背景,但他们懂得如何筹款,如何聚集所有资源来建造超级计算机。所以,这种方法对Sam Altman来说特别合适,因为这符合他擅长的东西。
方可成:他最擅长什么?
郝珂灵:他最干的就是能讲故事,讲未来的故事,他可以想象未来是什么样子,然后创造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让投资人、科学家、别的企业家都想加入他的使命,来构建他想象的未来。
但是他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因为他给不同的人讲的故事会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他会说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人工智能特别好,如果我们能更快地开发这个技术,它会把我们带到乌托邦。有时候会跟别人说人工智能是一个很可怕的技术,所以我们要拼命去开发人工智能,然后控制这个发展,不要分享给别人,让我们自己留着,慢慢地训练出一个更好的版本。
所以有人认为他是这一代的乔布斯,但另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喜欢撒谎的人,会慢慢地不太信任他。但是因为他讲故事讲得特别强,就很能筹钱。筹钱这方面,他真的很擅长。
方可成:所以他们组成了这个团队,有了一个其实当时坚信这样一种方法的科学家,然后有这些企业家支持,特别是有一个非常会拿钱的人,因为这个方法显然需要非常多的金钱投入才可以,所以这些才促成了OpenAI开发ChatGPT以及之后的所有这些模型。
你实际上是在2019年就已经去过OpenAI采访,对吧?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吗?
郝珂灵:OpenAI是2015年底创立的,当时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说我们要做基础AI研究,我们不要做什么商业产品,也不要卖什么东西,要用一个完全非营利的环境慢慢地去探索人工智能,去发展这项科技。因为Elon Musk特别担心,他觉得如果在一个营利的环境下发展人工智能的话,事情会变得很糟糕——而他觉得糟糕的意思是:AI会发展出意识,会发展出情感,会失控并且杀死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但是到了2017年,就是一年半之后,他们就开始确定这个规模化方法。他们开始讨论要从非营利转成营利,因为他们要钱,非营利如果想筹集那么大笔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他们开始讨论营利的时候,Elon Musk和Sam Altman都想当这个营利机构的CEO。当时其他两位倾向于Elon Musk,因为他们觉得Musk会把公司做得更成功。但是,Sam Altman就慢慢地开始跟Greg和Ilya说,你是不是觉得Musk有点太不可靠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公司交给他,人工智能以后发展的环境会不会不那么好?所以慢慢地就说服了Ilya Sutskever和Greg Brockman选他当CEO,而Musk就离开了。
所以我2019年去OpenAI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偷偷地开始做这个规模化方法,但是还没有跟别人说。他们当时没有完全转成一个营利机构,而是在非营利组织里边创建了一个营利部门。今天OpenAI还是那种结构,既有非营利也有营利。当时他们就跟我说,这种方法最好,因为我们确实要筹集很大一笔钱,但是我们还是想保持我们以前这个非营利使命,所以做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结构来制衡自己。虽然我们确实会以后可能要讨论怎么样去做产品,怎么样去商业化,但会被非营利的使命所管理。
方可成:那你在2019年采访的时候,当时有没有预料到后面这一系列从ChatGPT发布开始的轰动和发展?你当时觉得能看到未来的一些端倪吗?
郝珂灵:完全没有看到,因为当时我觉得他们的技术没有那么有意思。当时就是GPT-2,比ChatGPT早两代。GPT-2可以说可以写,但是写得也不好。这个模型本质上就是统计学,它讲的这些话虽然可以看起来有点像我们写的、说的,但它不是从同样的内在意义产生这些话。所以,我当时就没有意识到有了ChatGPT以后会那么轰动。

2024年8月,谷歌在乌拉圭卡内洛内斯建立新的数据中心。图源:谷歌博客
机器要“喝”干净的水,人要“洗”脏数据
方可成:你刚才说到了这种规模化的方法所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夸张的,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比较直观的例子,说明一下它是有多么夸张?
郝珂灵:好的。最近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显示,在5年之内,如果我们要继续维持超级计算机的发展来支持这种AI开发方式,我们必须在全球电网中增加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每年消耗能源的2到6倍的电力。而且,其中大部分必须来自化石燃料,因为这些数据中心不能只靠可再生能源来训练这些模型,也不能只靠可再生能源来部署这些模型。所以,我们实际上正在单方面逆转过去十年在气候方面取得的许多进展。
方可成:所以就是因为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技术,所以我们不得不又重新使用很多化石能源。
郝珂灵:没错。另外,目前这些工具的开发还需要大量纯净水来冷却数据中心。而且必须是纯净水,因为其他类型的水会导致细菌滋生并腐蚀设备。彭博社最近有一篇报道说,三分之二的这些数据中心已经进入了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的社区,所以训练这些模型实际上是在与社区的水资源竞争。
我在书里描述了南美洲的一个社区。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旱灾。就在那次旱灾期间,市政府不得不开始将有毒的水混入公共供水系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公共用水。所以很穷的人就在喝有毒的水,而且当时有很多怀孕的女性,她们的流产率更高,因为她们在喝这种水。
方可成:而与此同时,机器却要喝干净的水。
郝珂灵:那时,谷歌提议在那个城市的中心建造一个数据中心,这将消耗大量的纯净水资源。
方可成:为什么会是这些地方呢?明明知道这些地方缺水,为什么还会去这些地方提议要建数据中心呢?
郝珂灵:因为现在基本上没有那么多地方不缺水了,这是一场全球气候危机。其实基本上就是没有足够的地方来满足这些数据中心的需求了。随着AI对资源需求的增加,气候危机也在加速。我们看到这两个轨迹的碰撞,所有这些数据中心现在都建在已经受到气候危机影响的地方。
方可成:你刚才介绍了环境资源上的代价,你在书里也提到了劳工方面的代价,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展开介绍一下?
郝珂灵:好的。OpenAI当时选择去训练这些大规模模型的时候,他们也做了另一个选择,就是为了满足大规模AI的数据需求,你必须从使用“干净的数据”转向使用“被污染的数据”,因为没有足够的干净数据。
方可成:什么是干净的和被污染的数据?
郝珂灵:干净数据指的就是,当你建一个数据集的时候,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因为那些都是你自己挑选出来的;而被污染的数据指的就是,从网上抓取大批数据,你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是谁制造出来的。
方可成:那可能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选某一份报纸的数据,那我清楚地知道这份报纸上面有什么内容,这就是干净数据;而如果我在一个网络论坛,或者我在微博、Twitter上面随意地抓取一些数据下来,这就是污染数据。
郝珂灵:对的。互联网上什么都有,数据很乱。但你需要大量数据。OpenAI这些公司,它们实际上不知道自己的数据里有什么。当我采访研究人员时,除了数据来源之外,他们说不出数据的内容。
当你从使用干净数据转换到使用污染数据时,你必须开始做内容审核。因为当你在污染数据上训练这些大规模模型时,里面肯定会有很多杂乱的内容,模型就会开始表现得很奇怪,开始说一些有毒、辱骂、仇恨的话,这不会是一个好的消费者体验。
我采访的一个社群是肯尼亚的数据劳工,OpenAI在公司从基础研究转向商业化的时候,雇佣他们来执行这种内容审核。那些肯尼亚劳工,他们日复一日地阅读互联网上最糟糕的内容,试图训练一个过滤器来识别那些内容,然后阻止它被生成给用户。这是一个包裹在GPT模型周围的过滤器,确保用户永远不会接触到有毒内容。但这意味着,数据劳工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我采访了一个人,他在涉性内容团队。所以他在阅读所有关于性虐待、儿童性剥削的内容。而且这不仅仅是从互联网上抓取的内容,OpenAI还在提示其AI模型去想象互联网上的性内容,最糟糕的那种性内容,以便有更多样化的内容供他标记。每天这样做几个小时后,他的性格完全改变了,本来很外向,但后来变得很内向,不想和妻子、继女说话。
他也无法跟他的妻子说他为什么改变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他的工作是来整天看性内容。听起来不像真的工作,也听起来是一个很羞耻的工作,所以他根本无法去解释这些性格的改变。慢慢地,他的妻子就开始怀疑他们的婚姻。
有一天,他妻子说自己晚上想要吃鱼,他就出去买了三条鱼。他回家以后,发现她们所有东西都没了,然后他妻子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我现在已经不认识你是谁了,我们不会再回来。
方可成:这种事情当时在发生,现在这些是否还在发生呢?技术发展到现在,是否还需要这么多的数据标注劳工?以及,现在是不是用AI本身也可以去做内容审核了?
郝珂灵:绝对还在发生。你不能让AI来做内容审核,除非你已经实现了真正的AI,也就是真正具有理解能力的AI。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还没有解决内容审核的问题。你以为AI发展那么好了,以后这些审核问题都会消失,但是没有消失,因为这些模型还没有那么聪明,它们并不能去真正地理解文本的实际意义。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人去做这些内容审核。虽然基本上这些公司已经把所有以前互联网的内容已经用光了,但是天天还有很多人在生成新数据,所以还是会有更多的内容审核要做。而且,以前是文本生成模型,现在还有图像和视频生成模型,它们也要内容审核。
我发现,OpenAI在印度还有另一个外包公司,雇佣当地人来做图像内容审核。那些员工也是天天看这些内容,他们甚至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图像,但是同样的性虐待、儿童性剥削内容。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现在你想想视频生成,他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永远不会停止,因为用户总会想新的方法去滥用产品,公司就要增加新的内容审核层。所以这就像猫鼠游戏一样,永远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需要过滤掉。
创新投资的悖论:资金集中于大模型,更优AI技术难以实现
方可成:你刚才说到,几年前当OpenAI选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相信的,甚至是有点鄙视他们的这种方式的。但现在他们好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有很多其他的AI公司也在发展。那如今AI行业里面大概的情景是什么样?采用这种由OpenAI开创的这种方法,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绝对的主流了?还是说其实是有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方式在开发AI?
郝珂灵: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在做其他的方式,因为没有别的钱来做。
方可成:钱也用光了?我们什么东西都用光了!
郝珂灵:是的。我前几天了解到,基于现在初创公司的筹资数据,大约50%的投资都集中在OpenAI和Anthropic上。所以不只是没有钱去做别的AI开发方法,甚至是没有钱去做别的所有创新。所有的钱都集中在这两家公司上面。
那些更大的科技公司,谷歌、微软、Meta,他们也基本上全把所有的资源都投资在了大规模AI模型开发上,不再做别的事情。
比如,谷歌虽然收购了DeepMind,但是DeepMind还是可以做自己的研究,所以DeepMind几年前开发了AlphaFold,就是一个AI模型能从氨基酸序列预测蛋白质折叠,去年就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可是现在,他们基本上没有那个资源去做这种发展了。OpenAI发布ChatGPT后,谷歌和DeepMind就合并成了一个AI实验室。
方可成:等于说其他的可能性其实是被吃掉了。
郝珂灵:是的,所有的资源都去了大语言模型开发。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技术有多好,就是因为OpenAI的ChatGPT看起来是一个能杀死谷歌的产品——这个技术不是一个好的搜索引擎,但是很多人会拿它当作搜索引擎来用,所以谷歌投资这个技术其实不是来开发市场,而是为了保卫他们现在的市场。但是他们所有的资源已经用在了这个技术上面,所以别的创新像AlphaFold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投资了。
百度是一样的,当时ChatGPT出来的时候,我在《华尔街日报》报道百度。百度以前在AI医疗方面、AI药物发现方面做了很多投资,因为李彦宏对那个方面比较有兴趣,但是后来,他们所有的计算机芯片都转到了文心一言开发。所以,那些做AI医疗、药物的团队没有芯片去训练他们的模型了。
方可成:大家可能会马上想到DeepSeek。那么,DeepSeek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郝珂灵:DeepSeek还是大语言模型,所以也不是完全不一样,但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用的计算资源少很多。OpenAI这样的公司经常会说,我们必须得用这些资源去发展这个技术,而且这个技术特别重要,所以成本是值得的。但DeepSeek戳破了这个虚假的表象:其实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技术的很多好处,而且不需要这么大的成本。
如果我们继续做研究,我们很可能能够找到更好的技术来,用更少的成本开发AI。但是,我们没有资源投资在这些其他方法上。
AI帝国之下,不合作的可能性?
方可成:我接下来的问题是带有一点时间维度的,两个有一点相关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回过头看,当时如果不是Sam Altman的话,那历史是不是会不一样?历史是被个人创造的吗?还是说是必然发生的,不是Sam Altman也是一个John Altman或者另一个人创造出一样的轨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走到今天了,那我们之后还能怎么去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明天?
郝珂灵:写完这本书以后,我确实觉得:如果不是Sam Altman的话,我们可能不会在这个ChatGPT的世界里。因为Sam Altman为并不make sense的生意筹集资金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是别的人在当时担任OpenAI CEO的话,我认为他们会很快就达到资本上的限度,就是他们能说服投资者给这个技术的资金量的限制。但是,Sam Altman筹到的钱好像就是没有限制,这真的很厉害,也很可怕。
现在ChatGPT发布之后已经有差不多三年时间,OpenAI的业绩记录真的很平庸。我们没有看到特别大的经济生产力提升,没有看到那么多企业应用案例或成功的商业模式。所有这些公司,包括OpenAI都没有盈利能力,它们每个月都在烧掉数十亿美元,但是还是能筹款,钱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涌入。
所以我不喜欢伟人叙事,就是一个人能给历史发展轨迹带来这么大的区别,但是我是觉得他比较独特。当然,有多个交叉的趋势,但他恰好在正确的时刻定位自己,让他的特定技能组合发光。
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我认为同样地,我们如果能从Sam Altman学一样东西,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现在都能意识到,我们实际上在塑造AI的未来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十年后拥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方可成:如果我们不是那种会搞钱的,或者说我也不是一个AI工程师,那我还真的是有自己的作用吗?
郝珂灵:我会想到AI开发和部署的完整供应链,需要各种不同的东西去创造它们的技术,数据、土地、能源、冷却数据中心的纯净水,所有不同的空间用来部署他们的技术——学校、医院、公司、政府机构,如果这些地方不购买它们的服务,那么技术就不会在那里。
所以这些公司,尽管它们很强大,但它们实际上需要人们的合作。它们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合作,来给他们资源,并给他们进入这些空间的权限。有很多社区记住了这个事实,他们不合作。这些公司就必须改变。
有艺术家和作家正在起诉这些公司侵犯他们拿走的知识产权,这就是他们不合作:不,你不能只是拿我们的数据,而不给我们回报。这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拿我们的数据,而是说,你不能在不向我们提供互利协议的情况下拿走我们的数据。
世界各地有数百个社区在数据中心开发方面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说,不,你不能只是在我们的土地上建数据中心。你不能只是使用我们的能源和使用我们的水,提高我们的水电价格,让我们的电网更不可靠,仅仅因为你想建造这个对我们没有真正帮助的技术。你必须给我们一些互利的协议作为回报。
教师和学生也开始这样做。学校开始实施AI治理政策:在什么情况下,AI实际上会帮助培养我们的教育环境,提高下一代的批判性思维。其中一些学校已经决定完全禁止AI进入他们的学校环境。这是一种立场,为这些公司提供了一个压力点,这是他们损失掉的客户。
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接触AI供应链的多个不同部分。如果我们都使用这些不同的接触点来声张我们对这种技术的要求,我们实际上会到达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
方可成:是的。我听你在回答的时候,我就想到你这本书的标题“AI帝国”。既然AI的帝国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在这种帝国之下,具体的个体还有没有什么反抗的空间?很多人会合作,有一些人会逃避,但是可能还有些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抗。但是帝国的崩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实是非常难以预测的,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些看起来很偶然的原因就导致它的崩溃了。
郝珂灵:是的,但是历史上所有的帝国都会崩溃,因为它们的基础其实特别弱,它们是建立在剥削和榨取的逻辑之上,这不是长期可持续的。没有社会愿意永远存在于这种状态下,这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承诺。
如果这些公司永远不会给他们剥削和榨取的社区任何回报,这些社区当然会感到不满并停止允许他们这样做。这就是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倒台的方式——人们集体行动,抗议这种不公待遇和剥削,因为他们受够了。
方可成:你过去一个多月都在做这个新书宣传,会接触到很多的人,你觉得现在大家对AI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在想,要导致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公众舆论可能需要一个很大的转变才行。
一个类比是人们对社交媒体的态度。其实“过滤气泡”这个空间本身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我对社交媒体的很多反思和批判。五年前的时候我就在想,社交媒体五年之后大概应该消失吧?我们应该到下一个阶段了。但是到了2025年,我们每个人还在社交媒体上,包括我在做这个空间,也不得不利用社交媒体来做推广。我觉得好像望不到尽头了,好像我们就是永远都在社交媒体时代了。
但是当我私下跟Karen表达这些的时候,她当时就鼓励我说:其实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其实做现在这个空间,包括很多人开始出书,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探讨社交媒体对人的危害,心理上的危害、社交关系上的危害,虚假信息的危害……其实这个事情已经是10年前、15年前不太能够想象的。那时可能是一个非常乐观主义的对社交媒体的描述,觉得它会让所有人连接,它会让独裁政权倒台,它会带来各种各样有益的变化,但是现在我们的这种普遍的感觉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了。
所以我在想说,对AI的态度或许也会一样。也许我们再过10年,回头发现,哇,现在我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好大的变化,而也许这个变化的转折点就是Karen Hao的这本书出版了。
郝珂灵: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让公众对话更有层次。而且我在新书宣传的时候,确实发现很多人对我书中的信息非常能够接受。人们在读我的书之前对人工智能可能没有什么了解,而且更容易接受公司的典型叙事,这个科技有多么好,但一旦他们读了这本书,就立即连接到他们的一种已经有的感觉,那就是:他们越来越失去对技术的控制,他们不再过着一种技术为他们服务的生活,而是感觉他们在为技术服务。我真的不用说服人们,我对这真的觉得惊讶。就是我一开始讲关于帝国的论证,他们基本上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他们已经有了那种感觉,而我是在阐述一种他们一直试图描述的感觉。
萨姆·奥特曼被踢出公司的内幕
方可成:很多人还很关心的一点,就是关于Sam Altman中间一度被踢出公司的这一段故事八卦,我不知道Karen有没有一些内幕跟我们分享。
郝珂灵:这个情况在书里描述得挺详细的,有三章都在讲这个,有对话,有董事会成员互相说的话。简单来讲就是有两个事情发生,一个是很多人觉得Sam Altman不是很值得信任的领导者。第二个是,在整个大规模AI开发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意识形态冲突,就是在所谓的“繁荣派”和“末日派”之间,繁荣派认为AGI会带来乌托邦,末日派认为AGI会杀死所有人。当这种冲突在OpenAI内部发生的时候,董事会更倾向于末日派,因此更倾向于认真对待关于Sam Altman不值得信任的指控。
同时,有两位高管,首席技术官 Mira Murati和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由于各自独立的原因感到Altman不再是经营公司的合适人选,并向董事会表达了他们对此的严重担忧。董事会也独立地,由于其他原因,对Altman失去了很大信任。所以基本上,有五个人都独立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觉得Altman不应该被信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自己与Altman的人格冲突。最终,经过一系列非常激烈的讨论,董事会得出结论:他不是这个工作的合适人选。
但是这五个人中没有人想到的挑战是,正因为Sam Altman非常擅长筹钱,所以他一直是筹集大量资金的核心人物。有一个员工股权出售计划,让一些员工能够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兑现他们的股份。如果他离开,那么所有的钱都会消失,这就让组织变得不可持续。
所以,在投资者、微软、员工的巨大压力下,每个人出于各种原因,但都交汇在他是掌握金钱钥匙的人这一事实上,所以他被带回来并重新担任CEO。
方可成:所以钱真的很重要。关心更多细节的朋友可以在书里面详细阅读。
吉祥起名网 吉祥起名网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少儿武术 苏州武术 苏州少儿武术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